事隔一年半的Pranava造樂者安哥場,框架跟去年 一樣,然而舞台曲目都換上新裝,可是,廣東歌確實少了一點。
跟去年的曲目相比,其實是沒那麼「大路」,有朋友說像台灣演唱會加《歌手》。其實能夠聽到她的國語歌《誘惑的街》、《不必在乎我是誰》、還是別人的《多得他》、《無心睡眠》,確實也很興。可是,總覺得不夠滿足,好像心裡還有一個小小的缺口。這些曲目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我也全盤接收,唯獨香港,就是有那麼的一點點執著。當然香港歌迷愛聽憶蓮的廣東歌是正常不過的事,然而思前想後,我們有所失落,或許是大家不甘於香港作為巡迴演唱會的「香港站」,不要巡迴中的大同小異,渴望獨一無二。香港是起點,是發源地。
早於九十年代已打入台灣市場,今天更征服神州大地,然而最早的路,我們跟著她一路走過來,看著她三級跳,像羚羊般飛耀,見證她登上一個又一個高峰。
流行音樂就是有種魔力,是時代印記,我們通過歌曲能夠穿越時空,然而這不一定只是懷舊,而是重溫今天的路是怎樣走過來。還記得去年在台北造樂者,當《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前奏響起時,全場哄動,相信這個場景只會在台灣出現,因為這是她的第一首國語歌。紅遍大中華樂壇的是抒情慢歌,在香港的路卻是不一樣的風景,我常認為每次演唱會跳舞歌曲一環一定是香港專屬,從《灰色》走到都市觸覺年代,那是憶蓮的一大成就。我們要的不經典金曲演唱會,期盼冷門歌、等待滄海遺珠,也樂見重新創作,只有在香港,演繹這些歌曲才最有意義。
能夠征服大中華,我為她感到無比驕傲。然而渴求廣東歌,不代表「大香港」, 大中華很大,香港很小,很小卻變得親密親切,獨一無二。
可喜的是,一如以往,之後rundown 已有所改動,加了不少廣東歌。其實我們也不是那麼狹隘,只是過去的大豐盛,我們捨不得,我們太念掛,也難得,大家還在跟著你走。
Friday, November 10, 2017
音樂家沒法討厭政治 (明報:2017年10月15日)
這個黑色星期五傳來壞消息,著名指揮家杜達美(Gustavo Dudamel) 率領的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被委內瑞拉政府取消即將開展的亞洲巡演,當中包括11月香港藝術節舉辦的《貝多芬第一至第九交響曲》五場演出。杜達美在面書表示「委內瑞拉政府再次取消亞洲巡演,我的心也碎了。」 沒錯,是再次,早前九月的美國演出也被總統辦公室取消。兩次取消的原因也不明,政府從沒公開解釋,不過早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曾在電視中對杜達美說: 「Welcome to Politics!」,你看到的是政治干預藝術,還是藝術家不應談政治?
不要以為杜達美一直是委內瑞拉政府的眼中釘,現年36歲的杜達美可說是委內瑞拉的最佳文化大使,生於委內瑞拉的音樂世家,自小參加「El Sistema」音樂教育學習計劃,18歲已擔任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指揮,28歲那年成為洛杉磯愛樂樂團指揮,是該團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常任指揮。蜚聲國際後杜達美仍繼續擔任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帶領樂團走向國際。事實上,因為 一直避談國內的政治問題,被很多人批評。今年四月委內瑞拉的反政府示威不斷,抗議總統馬杜羅的獨裁。 一名由El Sistema訓練 的18歲小提琴手Armando Cañizales在一次示威中被鎮壓的警察擊斃,這位曾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的指揮家終於開腔發聲,公開譴責政府:「enough is enough」。到了七月在《紐約時報》 繼續發炮,反對馬杜羅推動修憲選舉。馬杜羅亦還擊,指他生活在外地不要對國事指點,然後又說「Welcome to politics」,不久總統辦公室便取消了九月份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在美國的巡演。有說可能是經濟問題,通賬嚴重,出訪經費太昂貴。亦有說是因為美國今年宣布制裁馬杜羅,兩國關係緊張,此舉是報復行為。取消美國巡演的消息早已成為西方國家頭條新聞,當時還沒有人擔心亞洲行程也會受阻,豈料在展開亞洲之旅首站台北的一星期前,主辦單位收到消息,指樂團無法成行,決定取消所有亞洲巡演,包括台北香港和廣州。香港藝術節在星期五發出新聞稿,宣布11月2至6日的音樂會及相關的公開彩排及社區探訪計劃全部取消,有關退票安排可到香港藝術節網站查詢。
其實杜達美不是第一次訪港,他跟洛杉磯愛樂樂團在2015年首次到訪,在香港藝術節演出,更在演出前與傳媒會面,還記得當天他在台上,記者們在台下,有一點朝聖的感覺。不過台上的杜達美盡情展示年輕的活力與熱情,有問必答表現親民。洛杉磯愛樂樂團主席及行政總裁Deborah Borda曾說杜達美﹙ Gustavo Dudamel ﹚帶給樂團最寶貴的東西,除了他的天賦才華,還有音樂的社會面向。杜達美在此事件後在面書表示,「希望年輕樂手堅強面對,我不會放棄捍衛言論自由和維護社會公義。」似乎今天的杜達美更明白音樂與社會政治是分不開。要一暏杜達美的風采其實也不難,身為洛杉磯愛樂團音樂及藝術總監,經常在國際舞台出現。今次被取消巡演的其實是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成員來自著名的音樂教育計劃El Sistema,杜達美便是計劃最成功的例子。El Sistema 由委內瑞拉音樂家與政治家José Antonio Abreu 於1975 年創立,為低下層的小孩提供音樂教育,他認為音樂能改變生命, 是藝術教育亦是品格教育,今天El Sistema分會遍佈全球,亦有無數被啟發而成立的藝術教育計劃,好像本地社企L plus H負責人何靜瑩創立的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便是以音樂劇推行品格教育。這次的亞洲之旅無法成行,焦點除了是杜達美不再沉默,敢於發聲對抗不公義外,更多的關注其實是El Sistema 計劃。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行政總裁Marshall Marcus 在《Guardian》的一篇文章指出,總統馬杜羅除子歡迎杜達美來到政治的世界外,更提醒他不要因為個人的行為而破壞了一班青少年的美麗活動。他指的正是El Sistema。作者說這個由政府資助的項目日後或許成為整治對像。事實上,兩次的取消行程已是一大警號。 其實現居美國的杜達美大可繼續來到亞洲與當地的樂團合作,他卻選擇與樂團共同進退,或許是為了保護這班年輕樂手。不知道購票入場的觀眾,有多少是慕著杜達美的大名,又有多少認識El Sistema? El Sistema 的口號是「to play and to struggle」,來到紛亂的時代,口號是否空談,實在顯而易見。
關於El Sistema 的著作:
《Changing Lives: Gustavo Dudamel, El Sistema, and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Music》
不要以為杜達美一直是委內瑞拉政府的眼中釘,現年36歲的杜達美可說是委內瑞拉的最佳文化大使,生於委內瑞拉的音樂世家,自小參加「El Sistema」音樂教育學習計劃,18歲已擔任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指揮,28歲那年成為洛杉磯愛樂樂團指揮,是該團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常任指揮。蜚聲國際後杜達美仍繼續擔任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帶領樂團走向國際。事實上,因為 一直避談國內的政治問題,被很多人批評。今年四月委內瑞拉的反政府示威不斷,抗議總統馬杜羅的獨裁。 一名由El Sistema訓練 的18歲小提琴手Armando Cañizales在一次示威中被鎮壓的警察擊斃,這位曾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的指揮家終於開腔發聲,公開譴責政府:「enough is enough」。到了七月在《紐約時報》 繼續發炮,反對馬杜羅推動修憲選舉。馬杜羅亦還擊,指他生活在外地不要對國事指點,然後又說「Welcome to politics」,不久總統辦公室便取消了九月份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在美國的巡演。有說可能是經濟問題,通賬嚴重,出訪經費太昂貴。亦有說是因為美國今年宣布制裁馬杜羅,兩國關係緊張,此舉是報復行為。取消美國巡演的消息早已成為西方國家頭條新聞,當時還沒有人擔心亞洲行程也會受阻,豈料在展開亞洲之旅首站台北的一星期前,主辦單位收到消息,指樂團無法成行,決定取消所有亞洲巡演,包括台北香港和廣州。香港藝術節在星期五發出新聞稿,宣布11月2至6日的音樂會及相關的公開彩排及社區探訪計劃全部取消,有關退票安排可到香港藝術節網站查詢。
其實杜達美不是第一次訪港,他跟洛杉磯愛樂樂團在2015年首次到訪,在香港藝術節演出,更在演出前與傳媒會面,還記得當天他在台上,記者們在台下,有一點朝聖的感覺。不過台上的杜達美盡情展示年輕的活力與熱情,有問必答表現親民。洛杉磯愛樂樂團主席及行政總裁Deborah Borda曾說杜達美﹙ Gustavo Dudamel ﹚帶給樂團最寶貴的東西,除了他的天賦才華,還有音樂的社會面向。杜達美在此事件後在面書表示,「希望年輕樂手堅強面對,我不會放棄捍衛言論自由和維護社會公義。」似乎今天的杜達美更明白音樂與社會政治是分不開。要一暏杜達美的風采其實也不難,身為洛杉磯愛樂團音樂及藝術總監,經常在國際舞台出現。今次被取消巡演的其實是委內瑞拉西蒙.玻利瓦爾交響樂團,成員來自著名的音樂教育計劃El Sistema,杜達美便是計劃最成功的例子。El Sistema 由委內瑞拉音樂家與政治家José Antonio Abreu 於1975 年創立,為低下層的小孩提供音樂教育,他認為音樂能改變生命, 是藝術教育亦是品格教育,今天El Sistema分會遍佈全球,亦有無數被啟發而成立的藝術教育計劃,好像本地社企L plus H負責人何靜瑩創立的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便是以音樂劇推行品格教育。這次的亞洲之旅無法成行,焦點除了是杜達美不再沉默,敢於發聲對抗不公義外,更多的關注其實是El Sistema 計劃。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行政總裁Marshall Marcus 在《Guardian》的一篇文章指出,總統馬杜羅除子歡迎杜達美來到政治的世界外,更提醒他不要因為個人的行為而破壞了一班青少年的美麗活動。他指的正是El Sistema。作者說這個由政府資助的項目日後或許成為整治對像。事實上,兩次的取消行程已是一大警號。 其實現居美國的杜達美大可繼續來到亞洲與當地的樂團合作,他卻選擇與樂團共同進退,或許是為了保護這班年輕樂手。不知道購票入場的觀眾,有多少是慕著杜達美的大名,又有多少認識El Sistema? El Sistema 的口號是「to play and to struggle」,來到紛亂的時代,口號是否空談,實在顯而易見。
關於El Sistema 的著作:
《Changing Lives: Gustavo Dudamel, El Sistema, and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Music》
去掉語言 以舞提煉雷雨 (明報: 2017年9月15日)
說起《雷雨》,隨即想起經常在粵語長片中看到「詩禮傳家」牌匾 ,意味著某種舊時代的精神。
今天再看《雷雨》,怎樣演繹「詩禮傳家」,怎樣去掉舊時代的味道,才可以呈現作品的精髓。鄧樹榮選擇去掉語言,同時以跨界方式重新演繹經典,把四小時的戲劇提煉成七十分鐘的舞劇,穿著旗袍馬褂的舞蹈員,用身體說故事,用故事告訴你中國舞的各種可能。
是經典再造,也期望再創經典。
文:林喜兒
圖:鄧樹榮戲劇工作室
鄧樹榮、邢亮與梅卓燕這個組合可能很容易引起觀眾一些聯想,而鄧樹榮和邢亮早在2009年已為香港舞蹈團創作了具實驗性的《帝女花》,這次也可以說是一種延續,再找來梅卓燕,揀選另一經典《雷雨》。「運用家傳戶曉的作品,以舞蹈和形體呈現,強調劇本的精神而不是語言和對白。」鄧樹榮形容《舞・雷雨》 就是運用舞蹈和形體劇場的語彙去呈現劇本的精神和人物關係。
「在這個基礎上,我刪掉了《雷雨》八個角色中的兩個,集中在引致悲劇發生的六個人物,誰和誰,發生了甚麼事,就是周萍與四鳳,周萍同蘩漪,四鳳與周冲,周樸園與魯媽,魯媽與四鳳,當中會有一些獨舞,再加上大結局。簡單地以故事提練人物關係和戲劇張力,然後透過舞蹈表達。」梅卓燕和邢亮根據這些故事情節編舞,鄧樹榮則以形體劇場連接舞蹈與舞蹈之間的過渡,以日常生活的動作串連。「這個合作方式頗有效,成功將四小時的戲劇轉化成七十分鐘的舞劇。」
創作於1933年,背景是民國時期的天津,一個世紀後在不同亞洲城市再現的《雷雨》,沒有加入甚麼新元素以回應新時代,反之卻是忠於原著。「《雷雨》是經典作品,劇本自有過人之處,嚴守三一律,故事發生在24小時內。我認為這個經典還有很多咀嚼的空間,特別是人物刻劃,戲劇張力很強,今天看還是感受到這股力量,縱使當中語言的運用不並適合這個年代。」《雷雨》這齣戲寶在國內自然是長做長有,鄧樹榮提到早前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再次上演《雷雨》,年輕觀眾聽到某些對白忍不住發笑。「舞蹈便不會出現時代的差距,用舞蹈去表達觀眾反而會更投入。其實這也印證了動作與語言之間的優劣,語言可以很精準,但不夠想像空間,相反動作有很多想像空間,但不可以很精準地表達。這次將舞蹈和戲劇結合為一,懂得《雷雨》的觀眾會看到這樣轉化,而不認識的也明白這個劇本的精髓。」《舞・雷雨》第一個畫面是六位主角坐在沙發準備拍照,當中已隱隱看到這六個人之間的關係。舞與劇的融合,便是這樣一回事。
要將戲劇的元素放進舞蹈動作中,鄧樹榮讓舞蹈員先上形體劇場工作坊。「我會將舞蹈歸類為形體劇場的一種,兩者也是關於表達與感受,不過舞者在感受這一環卻不太有戲劇意識,他們可能會有想法,但不會是很清楚的戲劇處境,而今次他們跳舞時也要有特定的戲劇處境,舞蹈員也要看劇本,她們只是不說話的演員,用舞蹈表達而不是對白,對舞蹈員是很大的突破。」看上《雷雨》,除了是以嶄新手法演繹經典,鄧樹榮跟兩位編舞也希望藉此探討中國舞這個概念,「如果要籠統地分,可分為古典與民間舞,但其實中國舞是創造出來的概念,於是我提出了中國舞概念給他們思考,兩位都是中國舞出身,也跳了很多現代舞。結果我們發覺不需理會是否中國舞,而且堅持分類對創作不一定有幫助。」鄧樹榮形容《舞・雷雨》的舞蹈是結合中國舞語彙與現代舞的精神,切合戲劇處境和角色。「可以說是有機的混合,有些語彙一看就明白,另外再加上一些道具,像蘩漪和四鳳也拿著扇,還有服裝,周萍周樸園穿的是長衫馬褂,周聰穿恤衫西褲,魯媽四鳳穿小鳳仙裝,在這種服裝架構下,舞蹈也要乎合其角色身分而發展。」
《舞・雷雨》於 2012 年新視野藝術節首演,在 2013 香港舞蹈年獎獨攬「最值得表揚編舞」、 「最值得表揚舞蹈劇作指導」及「最值得表揚女舞蹈員演出」三項大獎。隨後在新加坡、 台灣、 廣州 、北京、 南京巡演,今年九月回歸香港重演。所謂的經典,在不同華文世界也有不同反應,「原來台灣人不熟悉《雷雨》,因為從前曹禺被定為共產黨作家,新加坡也不太熟悉,但他們很欣賞這種形式。中國大陸固然很熟悉,但依然非常欣賞我們的手法,想不到只用六個舞者便可演繹《雷雨》。」
鄧樹榮近年積極發展形體劇場,一方面開展了「形體戲劇訓練課程」,另方面製作形體劇場作品,從《打轉教室》、《泰特斯》、廣東話《馬克白》等,在世界各地巡演,期望能創造經典。 「要成為經典,首先是演出是否有相當情度的感染力,不論內容和形式,不同觀眾看到也會有所感受,這是關於作品本身。另外就是營運上,要有不斷演出的機會,令不同觀眾有機會看到,這方面便有很多因素影響,自己的團去實行是非常困難,需要有合作伙伴,但他們的角色是甚麼?是買手?」今次在香港演出《舞・雷雨》的是江蘇省演藝集團歌劇舞劇院舞者,也是與該團的聯合製作。「這次的合作是另一種營運方式,由我負責排,交由另一劇團去演,但前題是對方喜歡你的作品。」
提到營運方面,鄧樹榮指出必須要有持續性,更要有策略,不過近年鄧樹榮的兩齣莎士比亞作品《泰特斯2.0》和《馬克白》卻在沒有計劃下在歐洲巡演。「自從2009年在倫敦環球劇場演出過《泰特斯》後,便加入了European Shakespeare Network,他們每年也會在歐洲舉行Festival,邀請不同城市的劇團參與。莎士比亞是世界文化遺產,更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渠道。以我們的方式演繹莎士比亞從而打入國際市場,這是完全沒有計劃,也沒有想過。」今年夏天,《馬克白》已巡迴六個城市, 做了八年的《泰特斯2.0》亦遊了三個城市。「我的藝術語言和風格比較容易走進國際市場,今天外國說起香港的莎劇便會想起我。」不過鄧樹榮也提到,語言不一定是阻礙,廣東話不一定沒有國際市場,「我們在香港不時有機會看到其他語言的作品,所以問題是香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而其實我們是做到的,只是在現行的文化生態和體制是相當困難。所以現在的局面是在香港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作品,但自己的卻走不出去。」
不要說巡演,要在香港重演也是異常困難。香港人都愛世界著名,喜歡國際大師,有沒有想過,我們也有國際大師?
編舞梅卓燕這樣說:
「很多舞蹈團的舞劇都很簡單,而且以往跳舞的人總覺得說故事老土,認為舞蹈不適合說故事,但看到同是用身體表達的形體劇場卻可以把故事說得很好,其實只是舞蹈對於戲劇表達比較粗疏,而舞蹈員的身體也沒有戲劇的意識。所以這次舞與劇也很平均,不是分開,而且可以結合,變成更具表達力的身體語言。《雷雨》其實是涉及很多人的內心世界,當中有其曖昧性,有些情節現在看來很老土,但我們卻能夠將其感情狀態,不易說出口的感覺化成舞蹈,而舞蹈最擅長的正是曖昧,改以舞蹈形式表達情感,便顯得細膩而深刻。相反劇場是一句台詞就是一句話的意思,而肢體的表達方式 可以有很多變化,這也是舞蹈可愛的地方。每個藝術形式都有擅長和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找出當中最厲害的元素,借用來再豐富,就像這次舞蹈與劇場互補。
由於故事發生在中國,是女人穿旗袍年代,所以用中國舞蹈語言很適合,但我們沒有局限在中國舞上,只要是跟肢體語言有關的也會用上,而且我們也不會分得很清楚,好像當中用了朝鮮舞的韻律,而扇這個道具亦是乎合情節,當中也有轉化。我跟邢亮每人負責不同場面,不過有趣的是觀眾看完後,也猜得出那段是我,那段是他的創作。」
Sunday, September 3, 2017
穿衣有時也有地
下雨天,想起不屬於我們的雨衣。
認識Seasalt Cornwall這個品牌是源自朋友穿的一件雨衣,她在Cornwall 旅行時購買,特點是能夠遮風抵雨。這件紅色的雨衣很是吸引,隨即去認識一下這個品牌。
“our studios overlook St. Anthony’s Lighthouse and Falmouth Bay. All of our prints and designs are unique to us and reflect the beautiful place we live in and love….Cornwall.
設計師及品牌創辦人之一的Sophie Chadwick說,每一季的設計靈感,都是源自Cornwall 的不同地方。
如何體現這個理念?看她的雨衣便會很明白,位處英國西南端的Cornwall ,臨海多雨,沿海當風,卻享受著最多的陽光,是以一件能夠抵檔風雨,透氣通爽,最重要是色彩鮮豔的雨衣絕對是品牌的signature item。官方網站上清楚解釋他們的雨衣是用甚麼質料,怎樣防水,怎麼防風。然而作為外貌協會成員,目光自然放在繽紛的色彩上,而且兼備不同長度,更有heavyweight 與lightweight 之分,選擇多多完全把我迷住,讓我好好記住Seasalt Cornwall 這個名字,成為to buy in UK 的top of the top。
幾個月前到Birmingham工幹,先是在Stratford 的小店遇上,時值大減價固然令人興奮,正因如此所以尺碼不齊。隔天就在John Lewis 給我遇上品牌的小專櫃,雖然款式不算多,但一排排衣架上掛著的美麗雨衣還是讓人非常心動,然而那一刻,突然變得非常冷靜,除了因為沒有折扣,如今每次買衫前都是停一停,諗一諗: 「是否會常常穿呢?」香港的下雨天都是熱得很,頂多只是三四月清明時節雨紛紛,卻仍然不需要勞思動眾穿一件遮風擋雨的雨衣。
我的衣櫃有兩件Seasalt Cornwall 的Tee,有機的那件非常耐洗,質料好的Tee就是值得投資,其實也只是二十多英鎊。回看Seasalt Cornwall 的設計,大概在雨衣和橫間Tee 外沒有甚麼適合我,那些碎花和圖案長裙也不是人人可以carry,一不小心便會變成村姑。
還沒有去過Cornwall,雨衣還是留待到英國買英國穿,常說「不時不食」,也應該有「不時不穿」。佩服好些朋友可以在香港的下雨天穿上雨靴,羨慕你們不怕熱不怕焗。穿衣要配合時地人,有時去某個地方旅行可能只為可以穿上某些衣服,想起衣櫃裡的大褸,這些年,似乎只有在外地冬天才可以走出衣櫥。
懷念四季分明的日子,面對地球暖化,少買為妙,不買就更佳。還在努力學習中,下次去英國,還是找一件二手的雨衣算了。
P.S. 除了衣櫃,書櫃也有三本Seasalt Cornwall的note book,依舊是海洋味十足的設計。
認識Seasalt Cornwall這個品牌是源自朋友穿的一件雨衣,她在Cornwall 旅行時購買,特點是能夠遮風抵雨。這件紅色的雨衣很是吸引,隨即去認識一下這個品牌。
“our studios overlook St. Anthony’s Lighthouse and Falmouth Bay. All of our prints and designs are unique to us and reflect the beautiful place we live in and love….Cornwall.
設計師及品牌創辦人之一的Sophie Chadwick說,每一季的設計靈感,都是源自Cornwall 的不同地方。
如何體現這個理念?看她的雨衣便會很明白,位處英國西南端的Cornwall ,臨海多雨,沿海當風,卻享受著最多的陽光,是以一件能夠抵檔風雨,透氣通爽,最重要是色彩鮮豔的雨衣絕對是品牌的signature item。官方網站上清楚解釋他們的雨衣是用甚麼質料,怎樣防水,怎麼防風。然而作為外貌協會成員,目光自然放在繽紛的色彩上,而且兼備不同長度,更有heavyweight 與lightweight 之分,選擇多多完全把我迷住,讓我好好記住Seasalt Cornwall 這個名字,成為to buy in UK 的top of the top。
幾個月前到Birmingham工幹,先是在Stratford 的小店遇上,時值大減價固然令人興奮,正因如此所以尺碼不齊。隔天就在John Lewis 給我遇上品牌的小專櫃,雖然款式不算多,但一排排衣架上掛著的美麗雨衣還是讓人非常心動,然而那一刻,突然變得非常冷靜,除了因為沒有折扣,如今每次買衫前都是停一停,諗一諗: 「是否會常常穿呢?」香港的下雨天都是熱得很,頂多只是三四月清明時節雨紛紛,卻仍然不需要勞思動眾穿一件遮風擋雨的雨衣。
我的衣櫃有兩件Seasalt Cornwall 的Tee,有機的那件非常耐洗,質料好的Tee就是值得投資,其實也只是二十多英鎊。回看Seasalt Cornwall 的設計,大概在雨衣和橫間Tee 外沒有甚麼適合我,那些碎花和圖案長裙也不是人人可以carry,一不小心便會變成村姑。
還沒有去過Cornwall,雨衣還是留待到英國買英國穿,常說「不時不食」,也應該有「不時不穿」。佩服好些朋友可以在香港的下雨天穿上雨靴,羨慕你們不怕熱不怕焗。穿衣要配合時地人,有時去某個地方旅行可能只為可以穿上某些衣服,想起衣櫃裡的大褸,這些年,似乎只有在外地冬天才可以走出衣櫥。
懷念四季分明的日子,面對地球暖化,少買為妙,不買就更佳。還在努力學習中,下次去英國,還是找一件二手的雨衣算了。
P.S. 除了衣櫃,書櫃也有三本Seasalt Cornwall的note book,依舊是海洋味十足的設計。
Sunday, August 13, 2017
《權力遊戲》 小野貓與籠中鳥
Arya 終於回家,與Sansa 相聚,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樣非常期待這一幕。
自從第一季Eddard Stark被斬頭,Stark 一家頓時流離失所,跟爸爸在
Kings’ Landing 的Sansa 和Arya,一個被困 ,一個流亡,各有各的凄慘和辛酸。兩人見面,說到回家的歷程,輕描淡寫地說: 「說來話長,不太愉快。 」兩人對望,面前的姊妹都長大了,從小女孩變成大人,過程真的不易。
Sansa 跟Arya的性格差不多是完全相反,一靜一動,一個內斂,一個率直,一個是公主,一個是男仔頭。第一季的第一集已經簡單直接地告訴你兩人性格迴異,13 歲的Sansa 很專心地學習刺繡,Arya 卻心不在焉,豎起耳仔聽著哥哥弟弟在外面練箭。喜愛吃lemon cake的Sansa是無知小女孩,一心一意要嫁王子。Arya 從來不喜歡做淑女,在不知不覺間更裝備起來,她的Needle 不是用來繡花,而是Jon Snow 送給她的劍,爸爸見她好此道,也安排老師跟她練劍,或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讓剪掉長髮,放下貴族身份 的Arya 披荊斬棘,成功脫險,最後更練得一手好劍法。上天像是安排Arya踏上這條復仇之路,機靈勇敢的Arya ,沿路遇上Tywin Lannister、Hound,Faceless Man Jaqen,Hound 兩次想賣她給母親和亞姨,卻每每遲了一步,註定了她不能依靠別人,沒有向北去找Jon Snow,卻去了Braavos 找faceless man,最後收成正果。
如果Arya 是小野貓,Sansa 便是籠中鳥。在King’s Landing被Joffrey 精神與暴力虐待,徬徨無助, 直至Margaery 出現成為Joffrey的皇后, 之後又被安排嫁給Tyrion Lannister。Purple Wedding 後跟著Little Finger 逃離King’s Landing,到Eyrie 找亞姨 Lysa Arryn,隨後Little Finger又把她嫁給Ramsay Bolton,慘被蹂躪。受盡折磨的Sansa 不再是無知的小公主,她睜開雙眼看著Ramasay Bolton 被犬決,然後笑著離去,與Jon Snow 回到家鄉Winterfell,Lady Sansa 更替Jon Snow 接管The North。
從一開始已喜歡Arya 這個角色,率真,勇字掛心口,有仇報仇,要殺便殺,一路跟著她歷險,好彩沒有安排她死去。Sansa這個等待被救的公主是越看越有味道,不再甘於被人操控,她明白到父親和兄長都是因為太愚(或者是太善良) 才導致如此結果。一個在朝中學懂政治,一個在野外變得勇武。Arya 說: 「你我的故事尚未完。」非常期待Stark 姊妹一文一武的復仇。

自從第一季Eddard Stark被斬頭,Stark 一家頓時流離失所,跟爸爸在
Kings’ Landing 的Sansa 和Arya,一個被困 ,一個流亡,各有各的凄慘和辛酸。兩人見面,說到回家的歷程,輕描淡寫地說: 「說來話長,不太愉快。 」兩人對望,面前的姊妹都長大了,從小女孩變成大人,過程真的不易。
Sansa 跟Arya的性格差不多是完全相反,一靜一動,一個內斂,一個率直,一個是公主,一個是男仔頭。第一季的第一集已經簡單直接地告訴你兩人性格迴異,13 歲的Sansa 很專心地學習刺繡,Arya 卻心不在焉,豎起耳仔聽著哥哥弟弟在外面練箭。喜愛吃lemon cake的Sansa是無知小女孩,一心一意要嫁王子。Arya 從來不喜歡做淑女,在不知不覺間更裝備起來,她的Needle 不是用來繡花,而是Jon Snow 送給她的劍,爸爸見她好此道,也安排老師跟她練劍,或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讓剪掉長髮,放下貴族身份 的Arya 披荊斬棘,成功脫險,最後更練得一手好劍法。上天像是安排Arya踏上這條復仇之路,機靈勇敢的Arya ,沿路遇上Tywin Lannister、Hound,Faceless Man Jaqen,Hound 兩次想賣她給母親和亞姨,卻每每遲了一步,註定了她不能依靠別人,沒有向北去找Jon Snow,卻去了Braavos 找faceless man,最後收成正果。
如果Arya 是小野貓,Sansa 便是籠中鳥。在King’s Landing被Joffrey 精神與暴力虐待,徬徨無助, 直至Margaery 出現成為Joffrey的皇后, 之後又被安排嫁給Tyrion Lannister。Purple Wedding 後跟著Little Finger 逃離King’s Landing,到Eyrie 找亞姨 Lysa Arryn,隨後Little Finger又把她嫁給Ramsay Bolton,慘被蹂躪。受盡折磨的Sansa 不再是無知的小公主,她睜開雙眼看著Ramasay Bolton 被犬決,然後笑著離去,與Jon Snow 回到家鄉Winterfell,Lady Sansa 更替Jon Snow 接管The North。
從一開始已喜歡Arya 這個角色,率真,勇字掛心口,有仇報仇,要殺便殺,一路跟著她歷險,好彩沒有安排她死去。Sansa這個等待被救的公主是越看越有味道,不再甘於被人操控,她明白到父親和兄長都是因為太愚(或者是太善良) 才導致如此結果。一個在朝中學懂政治,一個在野外變得勇武。Arya 說: 「你我的故事尚未完。」非常期待Stark 姊妹一文一武的復仇。

Sunday, July 30, 2017
街知巷聞﹕拼湊街坊回憶 還原李鄭屋徙置區 (明報星期日生活) 30-7-2017
輪到我做受訪者!
【明報專訊】因為要寫書,林喜兒才知道,住在母親樓上的八十歲老人蔡楚邦,是昔日一家人在徙置區時,樓下開士多的老闆。
「我識你老竇好耐,佢未結婚已經識,成日坐埋傾偈,大家潮州人,比較親切。」 一九五三年石硤尾發生大火後,殖民地政府大舉清拆寮屋,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流離失所的人由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蔡楚邦一家是火災後上樓的第一代李鄭屋徙置區居民。
後來,李鄭屋發生過兩件大事,一九五五年興建徙置大廈期間,發現了漢代古墓,一九五六年,第十座一名職員因為撕下了國民黨旗,引發雙十暴動,年輕的蔡楚邦剛下班,看到李鄭屋狀况,折回深井紗廠打算暫避風頭,怎料暴動蔓延開去,整個工廠的人被拉,他自己也被帶到紅磡車站附近的大包米集中營,關了五十多天。聽到這一段歷史,林喜兒思忖,當中會不會曾經有過父親的身影?
三十年燈火 映照一代人故事
「後來我回想起,我爸應該是第一代的徙置區居民,雙十暴動時,他也是後生仔來,不知道他有沒有被人拉?」記憶朦朧,隱約記得家中也曾出現青天白日旗,還有,父親生前一些念念碎碎﹕「有小小後悔,細個我爸成日講,但沒有耐性聽。」
父親遠去,坊間有關李鄭屋村歷史的紀錄從缺,惟這十九座七層大廈,由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四年完成清拆前,三十年燈火,構建了數以萬計香港人的共同記憶,簡陋的居所設計、生活方式,塑造了一整代香港人的性格,在很多年後的今天,仍然以某種姿態,活在我們之中。
帶着對這個成長地方的模糊印象,林喜兒透過臉書群組「李鄭屋村(七層高世代)」,逐一尋訪昔日左鄰右里,紀錄他們的口述歷史,寫下《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一書﹕「什麼龍蛇混雜的紅番區,回味無窮的平民美食天堂,還有那個像傳說一樣的鄰里關係……不想忘記過去歲月,卻不愛沉溺於往昔情懷,是好是壞,是笑是淚,也學習欣然接受。我想,這樣才能勇敢面對未來。」
忘不了的童年 貧困中玩耍
回憶,混雜而紛亂,只是都好似沒有冬天。
二十個訪問,二十塊記憶拼圖,有人拉開記憶的抽屜,看到不枉過的快樂童年,昔日的樓梯走廊彷彿是為小孩度身訂做的遊樂場所﹕「通常放紙鳶會先上去六七樓,然後把紙鳶放落二三樓,找人拉遠距離,再在樓上抽一抽才可以起鳶,我們就趁樓上放落街時偷了紙鳶,叫做『打飛陀』」、「如果碰到收買佬,便會將所有拖鞋拿去換麥芽糖」,鄰里關係,也可真如吳楚帆的粵語殘片中那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周家買了電視後繼續中門大開……個個自出自入,家家戶戶不關門,晚上十幾廿人,看《如來神掌》。」
聽着聽着,林喜兒將故事和自己的童年記憶對照,只有茫然﹕「只記得那時阿媽唔畀落街,附近龍蛇混雜,有道友又有黑社會,只可以自己在房裏玩,最記得好憎那個廁所,好臭。」她將這些無法共鳴的回憶,整理後收錄在〈我們的快樂時代〉一章,發現對徙置區留下類近印象的人,恰恰便是戰後嬰兒一代。
「他們有多少美化了那種徙置區的情懷。」今天五六十歲年紀,戰後一代成長於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歲月,在普遍香港人脫離貧窮經驗之前,於徙置區中度過了無憂童年﹕「他們會話舊時住喺嗰度好開心,個個打開門,那因為其實間屋細吖嘛,不打開門可以怎樣,你屋內的範圍其實是extend到外邊的,所以舊時街頭巷尾個個都識,大家互相幫助;又因為那時窮,屋企沒有東西比人偷,今天叫你打開門,你也不會吧。」
看不見的苦難 父母輩承載
懷緬過去常陶醉,他們記住了一半樂事,流淚的一半,由父母輩分擔在記憶之中﹕「掉返轉頭,訪問中接觸到七八十歲老人家,沒有像他們所說過得快樂,像我媽,常因為四圍都是白粉佬、黑社會而提心吊膽。」老人家分享的故事,圍繞着生活在徙置區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不安感,H字型的樓層,兩排單位中間連起來的地方是廁所、冲涼房和水喉腳,有人記得水喉腳是師奶們洗碗洗菜的聚「腳」點,因而得名,也有人記得曾經見過人偷狗,在水喉腳劏,然後拿去賣;父母在樓梯口守候夜歸子女,甚至陪伴他們去冲涼﹕「當時冲涼房沒門,很危險。」
但同時間,戰後嬰兒一代對於徙置區的苦同樣念念不忘﹕「通常都窮,我叫他們做家庭童工,全部小學起便要幫屋企做小販,落冰室幫手。」「問他們有沒有人來收黑錢,個個都會話有,有些甚至話,我老竇有份收的。佢哋成日話,啲差佬好衰,政府啲人好衰,對我哋好差,但掉返轉呢,佢哋又會話果時好開心,但我覺得矛盾位就係,明明你講緊那時的環境如此惡劣,為何當時你又這樣開心?」
每一次回望都是重塑
「我覺得他們是選取了來記憶。」每一次回望也是重塑,選擇性地提取記憶中的苦與樂,獅子山下,他們的徙置區總是歡笑多於唏噓﹕「有好多我接觸的人當中,會覺得我今天所有嘢都是自己捱回來的,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那種,對照不到現在,沒有體諒。」
昔日鄰舍情懷 今日重現社區
林喜兒在後記中反思﹕「我相信記載歷史不是要書寫美好……無意否定回憶中的美事,只希望不要過於浪漫化,與其說今天不及從前,倒不如實際一點,想想如何尋回昔日美事。」
「因為我做這本書不是想純粹懷舊,舊時你覺得好嘅嘢,你可不可以打開門和你的鄰舍關係做得好點?」昔日徙置區一代念茲在茲的鄰舍情懷,林喜兒看到它在今天年輕一代之間,以社區連結的姿態復興再現。
近年流行講外國的共居概念,不就是從前徙置區那種公私不分的概念?不過從前公共是被迫的,今天也沒有誰願意回到那種規格的居住單位,而倡議共居,是針對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疏離,在城市人口結構和高房價之下的折衷之法﹕「比如我其中一個受訪者同我講番,那時古墓旁邊,原來會放映電影的,那我便去檔案館查,發現當時政府會在徙置區做這些活動,因為沒有娛樂,今天流行講社區放映,其實那時已經有;又有些人會上門修理瓦煲,幫你磨餐刀鉸剪之外,原來還會上門幫你紮染衣服;徙置區樓下有一些回收的檔攤,大家會送舊玻璃去,現在我們講緊的一些概念,原來舊時是有的。」
提取過去的好,離棄醜惡,讓它在今天香港賦予新的意義,不正正就是歷史的任務?
「原來我們一直在追求那個時代美好的東西。」
徙置區由來
石硤尾大火後,工務局在火災原址興建了兩層高的「包寧」平房作應急之用(包寧是當時工務局長的名字),同時又興建了八座六層高的徙置大廈作試點,繼而開始在各區大規模建徙置區。徙置大廈設計簡陋,單位家徒四壁,主要用作安置受災或清拆的寮屋居民,而差不多同時期在一九五二年落成的上李屋邨,才是香港首個公共屋邨。
樓高七層
為什麼徙置區不多不少就只七層高?建築師衛翠芷認為,七層高必然是經過精密計算,一是因為電梯成本太高,二是要考慮地基能否承受,在這些限制下,七層應該是最高極限。
H型設計
重實用性,不花巧,沒有多餘的裝飾,能夠大規模倒模複製,難怪衛翠芷說,徙置大廈其實是現代主義建築。
H型的設計,由兩幢對望的大樓組成一對, 中間相連的部分除了是公共浴廁,設計還可以對照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中庭社區空間;不同的是宿舍大樓只有單排單位,每戶一邊是通風走廊,一邊是窗,相對徙置大廈為了要提供最多單位,將本來可以前門後窗的單位一劏為二,變相令到單位密封,卻意外造就了徙置區家家戶戶大開中門的獨有生態。
區長
即徙置事務處的地區主任,一名「區長」負責管理兩座徙置大廈,接近五千名住戶,除了日常管理,也負責地下樓層店舖的租務,自然撈不少「油水」,比如幾位街坊說起,不約而同提到,當年只要付區長300元便可獲安排多一個單位,嚴如行賄「公價」。
為食街
第四、五座對落空地是街坊口中的「為食街」,有冰室,大牌檔,士多,其中大家最記得財記的「沙嗲牛肉麵」,林喜兒找到當年在財記幫手的一對姐妹,記得當時舖頭常有一個人坐一旁數錢,後來才知道是爸爸准許他在店內賣白粉,有次爸爸被打劫,很快有差人幫手,游走於黑白兩道之間討生活,是那個年代的徙置區寫照。
《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
作者:林喜兒
分享會︰你記得的李鄭屋徙置區
時間︰8月6日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Wontonmeen
文﹕梁仲禮
圖﹕三聯出版社提供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明報專訊】因為要寫書,林喜兒才知道,住在母親樓上的八十歲老人蔡楚邦,是昔日一家人在徙置區時,樓下開士多的老闆。
「我識你老竇好耐,佢未結婚已經識,成日坐埋傾偈,大家潮州人,比較親切。」 一九五三年石硤尾發生大火後,殖民地政府大舉清拆寮屋,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流離失所的人由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蔡楚邦一家是火災後上樓的第一代李鄭屋徙置區居民。
後來,李鄭屋發生過兩件大事,一九五五年興建徙置大廈期間,發現了漢代古墓,一九五六年,第十座一名職員因為撕下了國民黨旗,引發雙十暴動,年輕的蔡楚邦剛下班,看到李鄭屋狀况,折回深井紗廠打算暫避風頭,怎料暴動蔓延開去,整個工廠的人被拉,他自己也被帶到紅磡車站附近的大包米集中營,關了五十多天。聽到這一段歷史,林喜兒思忖,當中會不會曾經有過父親的身影?
三十年燈火 映照一代人故事
「後來我回想起,我爸應該是第一代的徙置區居民,雙十暴動時,他也是後生仔來,不知道他有沒有被人拉?」記憶朦朧,隱約記得家中也曾出現青天白日旗,還有,父親生前一些念念碎碎﹕「有小小後悔,細個我爸成日講,但沒有耐性聽。」
父親遠去,坊間有關李鄭屋村歷史的紀錄從缺,惟這十九座七層大廈,由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四年完成清拆前,三十年燈火,構建了數以萬計香港人的共同記憶,簡陋的居所設計、生活方式,塑造了一整代香港人的性格,在很多年後的今天,仍然以某種姿態,活在我們之中。
帶着對這個成長地方的模糊印象,林喜兒透過臉書群組「李鄭屋村(七層高世代)」,逐一尋訪昔日左鄰右里,紀錄他們的口述歷史,寫下《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一書﹕「什麼龍蛇混雜的紅番區,回味無窮的平民美食天堂,還有那個像傳說一樣的鄰里關係……不想忘記過去歲月,卻不愛沉溺於往昔情懷,是好是壞,是笑是淚,也學習欣然接受。我想,這樣才能勇敢面對未來。」
忘不了的童年 貧困中玩耍
回憶,混雜而紛亂,只是都好似沒有冬天。
二十個訪問,二十塊記憶拼圖,有人拉開記憶的抽屜,看到不枉過的快樂童年,昔日的樓梯走廊彷彿是為小孩度身訂做的遊樂場所﹕「通常放紙鳶會先上去六七樓,然後把紙鳶放落二三樓,找人拉遠距離,再在樓上抽一抽才可以起鳶,我們就趁樓上放落街時偷了紙鳶,叫做『打飛陀』」、「如果碰到收買佬,便會將所有拖鞋拿去換麥芽糖」,鄰里關係,也可真如吳楚帆的粵語殘片中那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周家買了電視後繼續中門大開……個個自出自入,家家戶戶不關門,晚上十幾廿人,看《如來神掌》。」
聽着聽着,林喜兒將故事和自己的童年記憶對照,只有茫然﹕「只記得那時阿媽唔畀落街,附近龍蛇混雜,有道友又有黑社會,只可以自己在房裏玩,最記得好憎那個廁所,好臭。」她將這些無法共鳴的回憶,整理後收錄在〈我們的快樂時代〉一章,發現對徙置區留下類近印象的人,恰恰便是戰後嬰兒一代。
「他們有多少美化了那種徙置區的情懷。」今天五六十歲年紀,戰後一代成長於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歲月,在普遍香港人脫離貧窮經驗之前,於徙置區中度過了無憂童年﹕「他們會話舊時住喺嗰度好開心,個個打開門,那因為其實間屋細吖嘛,不打開門可以怎樣,你屋內的範圍其實是extend到外邊的,所以舊時街頭巷尾個個都識,大家互相幫助;又因為那時窮,屋企沒有東西比人偷,今天叫你打開門,你也不會吧。」
看不見的苦難 父母輩承載
懷緬過去常陶醉,他們記住了一半樂事,流淚的一半,由父母輩分擔在記憶之中﹕「掉返轉頭,訪問中接觸到七八十歲老人家,沒有像他們所說過得快樂,像我媽,常因為四圍都是白粉佬、黑社會而提心吊膽。」老人家分享的故事,圍繞着生活在徙置區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不安感,H字型的樓層,兩排單位中間連起來的地方是廁所、冲涼房和水喉腳,有人記得水喉腳是師奶們洗碗洗菜的聚「腳」點,因而得名,也有人記得曾經見過人偷狗,在水喉腳劏,然後拿去賣;父母在樓梯口守候夜歸子女,甚至陪伴他們去冲涼﹕「當時冲涼房沒門,很危險。」
但同時間,戰後嬰兒一代對於徙置區的苦同樣念念不忘﹕「通常都窮,我叫他們做家庭童工,全部小學起便要幫屋企做小販,落冰室幫手。」「問他們有沒有人來收黑錢,個個都會話有,有些甚至話,我老竇有份收的。佢哋成日話,啲差佬好衰,政府啲人好衰,對我哋好差,但掉返轉呢,佢哋又會話果時好開心,但我覺得矛盾位就係,明明你講緊那時的環境如此惡劣,為何當時你又這樣開心?」
每一次回望都是重塑
「我覺得他們是選取了來記憶。」每一次回望也是重塑,選擇性地提取記憶中的苦與樂,獅子山下,他們的徙置區總是歡笑多於唏噓﹕「有好多我接觸的人當中,會覺得我今天所有嘢都是自己捱回來的,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那種,對照不到現在,沒有體諒。」
昔日鄰舍情懷 今日重現社區
林喜兒在後記中反思﹕「我相信記載歷史不是要書寫美好……無意否定回憶中的美事,只希望不要過於浪漫化,與其說今天不及從前,倒不如實際一點,想想如何尋回昔日美事。」
「因為我做這本書不是想純粹懷舊,舊時你覺得好嘅嘢,你可不可以打開門和你的鄰舍關係做得好點?」昔日徙置區一代念茲在茲的鄰舍情懷,林喜兒看到它在今天年輕一代之間,以社區連結的姿態復興再現。
近年流行講外國的共居概念,不就是從前徙置區那種公私不分的概念?不過從前公共是被迫的,今天也沒有誰願意回到那種規格的居住單位,而倡議共居,是針對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疏離,在城市人口結構和高房價之下的折衷之法﹕「比如我其中一個受訪者同我講番,那時古墓旁邊,原來會放映電影的,那我便去檔案館查,發現當時政府會在徙置區做這些活動,因為沒有娛樂,今天流行講社區放映,其實那時已經有;又有些人會上門修理瓦煲,幫你磨餐刀鉸剪之外,原來還會上門幫你紮染衣服;徙置區樓下有一些回收的檔攤,大家會送舊玻璃去,現在我們講緊的一些概念,原來舊時是有的。」
提取過去的好,離棄醜惡,讓它在今天香港賦予新的意義,不正正就是歷史的任務?
「原來我們一直在追求那個時代美好的東西。」
徙置區由來
石硤尾大火後,工務局在火災原址興建了兩層高的「包寧」平房作應急之用(包寧是當時工務局長的名字),同時又興建了八座六層高的徙置大廈作試點,繼而開始在各區大規模建徙置區。徙置大廈設計簡陋,單位家徒四壁,主要用作安置受災或清拆的寮屋居民,而差不多同時期在一九五二年落成的上李屋邨,才是香港首個公共屋邨。
樓高七層
為什麼徙置區不多不少就只七層高?建築師衛翠芷認為,七層高必然是經過精密計算,一是因為電梯成本太高,二是要考慮地基能否承受,在這些限制下,七層應該是最高極限。
H型設計
重實用性,不花巧,沒有多餘的裝飾,能夠大規模倒模複製,難怪衛翠芷說,徙置大廈其實是現代主義建築。
H型的設計,由兩幢對望的大樓組成一對, 中間相連的部分除了是公共浴廁,設計還可以對照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中庭社區空間;不同的是宿舍大樓只有單排單位,每戶一邊是通風走廊,一邊是窗,相對徙置大廈為了要提供最多單位,將本來可以前門後窗的單位一劏為二,變相令到單位密封,卻意外造就了徙置區家家戶戶大開中門的獨有生態。
區長
即徙置事務處的地區主任,一名「區長」負責管理兩座徙置大廈,接近五千名住戶,除了日常管理,也負責地下樓層店舖的租務,自然撈不少「油水」,比如幾位街坊說起,不約而同提到,當年只要付區長300元便可獲安排多一個單位,嚴如行賄「公價」。
為食街
第四、五座對落空地是街坊口中的「為食街」,有冰室,大牌檔,士多,其中大家最記得財記的「沙嗲牛肉麵」,林喜兒找到當年在財記幫手的一對姐妹,記得當時舖頭常有一個人坐一旁數錢,後來才知道是爸爸准許他在店內賣白粉,有次爸爸被打劫,很快有差人幫手,游走於黑白兩道之間討生活,是那個年代的徙置區寫照。
《七層足印——李鄭屋徙置區口述歷史》
作者:林喜兒
分享會︰你記得的李鄭屋徙置區
時間︰8月6日
下午2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Wontonmeen
文﹕梁仲禮
圖﹕三聯出版社提供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Sunday, July 23, 2017
《七層足印》終於出版了!
從事文字工作多年,完全沒有想過要出書,反正寫字對我來說是工作也是興趣,而且總覺得出書有時只是一種虛榮。
曾經寫潮流寫旅遊,現在喜歡寫文化寫人物,這次出書,卻是關於口述歷史。自媒體當道,要發表甚麼偉論個人感想,不用勞思動眾搞出版,也沒必要浪費紙張。然而說到歷史,似乎有必要實實在在記錄下來。
我在書中這樣介紹自己,「從時裝潮流到旅遊玩樂,從藝術文化到人物專訪。現為自由工作者,努力書寫香港,記住香港。」
大概我下一本作品,也會是記錄,也是關於香港。
《七層足印》2017 香港書展三聯書局率先發售。
曾經寫潮流寫旅遊,現在喜歡寫文化寫人物,這次出書,卻是關於口述歷史。自媒體當道,要發表甚麼偉論個人感想,不用勞思動眾搞出版,也沒必要浪費紙張。然而說到歷史,似乎有必要實實在在記錄下來。
我在書中這樣介紹自己,「從時裝潮流到旅遊玩樂,從藝術文化到人物專訪。現為自由工作者,努力書寫香港,記住香港。」
大概我下一本作品,也會是記錄,也是關於香港。
《七層足印》2017 香港書展三聯書局率先發售。
Monday, June 12, 2017
記錄日常 (二) 切忌三心兩意
還在看Mason Currey的《 Daily Rituals》,作家大師藝術家的日常有意想不到也有平平無奇,不過讀著總覺有點距離,不是因為這些人已是神枱級,而是身處的時代不同。至少他們不用應付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誘惑,當wifi 變成空氣一樣時,光陰就是如此虛度了。
每次準備開工前例必要在網上無聊地漫遊熱下身,一不小心隨時看了齣電影或幾集電視。不過讓我最自責的不是瘋狂地煲劇,而是有時扮勤力扮乖,想早點完成工作,但實情是,先上網無聊無聊,又心思思想睇劇,搞下呢搞下路,眨眨眼,幾小時過去了,最後沒有一樣能夠完成,真的hea爆了!於是,我學懂了,在不想工作時就索性不做,乾脆努力煲劇吧!
上星期的時間表就是日間外出做瑜珈開會約朋友,晚上看劇,星期一追看新一集的 Silicon Valley ,星期二是 Better Call Saul,為了迎接七月Season 7,一星期重溫一季的Game of Thrones,然後甚麼也不寫! 到了星期六日大家休息的日子,我就在家寫字看書,一齣劇也不看。
一星期後,發覺即使一隻字都無寫,至少看了劇和書,總算有點成就吧!當然deadline來臨又是另一番光景。
我還是記得村上春樹說:「能寫的時候順著氣勢寫很多,寫不出來時就休息的話,就無法產生規律性。」規律,真的離我很遠。

每次準備開工前例必要在網上無聊地漫遊熱下身,一不小心隨時看了齣電影或幾集電視。不過讓我最自責的不是瘋狂地煲劇,而是有時扮勤力扮乖,想早點完成工作,但實情是,先上網無聊無聊,又心思思想睇劇,搞下呢搞下路,眨眨眼,幾小時過去了,最後沒有一樣能夠完成,真的hea爆了!於是,我學懂了,在不想工作時就索性不做,乾脆努力煲劇吧!
上星期的時間表就是日間外出做瑜珈開會約朋友,晚上看劇,星期一追看新一集的 Silicon Valley ,星期二是 Better Call Saul,為了迎接七月Season 7,一星期重溫一季的Game of Thrones,然後甚麼也不寫! 到了星期六日大家休息的日子,我就在家寫字看書,一齣劇也不看。
一星期後,發覺即使一隻字都無寫,至少看了劇和書,總算有點成就吧!當然deadline來臨又是另一番光景。
我還是記得村上春樹說:「能寫的時候順著氣勢寫很多,寫不出來時就休息的話,就無法產生規律性。」規律,真的離我很遠。

Friday, June 9, 2017
又一條掘頭巷
西營盤山道的保德街,相信大學年代必定路過,不過那時大概是沿著斜路走到下面的石塘咀熟食中心覓食,完全不會留意這條掘頭路。直至數年前茶。家落戶在街尾,然後是斜對面的Artisan Garden Cafe,我才知道這條掘頭巷叫做保德街。
西環一帶是香港最早開發的地區,相信這條街必定歷史悠久,然後我找到這張二十年代的保德街照片,整條街都是兩層高的唐樓。今天的保德街融合了舊鋪與新店,希望它不要變得火熱,如果這裡變得太熱鬧,就不再有趣了。
看起來平平無奇,其實是別有洞天,大街內的小巷,小巷內的小店,小店內的後欄,好像Artisan Garden Cafe 內的露天座位其實是個小天井,乾淨整潔,抬頭看到高樓與大樹,香港果真是石屎森林。不過可惜的是茶。家將於月底結業,又少了一個選擇。
舊相來源: http://hkgalden.com/view/107520

西環一帶是香港最早開發的地區,相信這條街必定歷史悠久,然後我找到這張二十年代的保德街照片,整條街都是兩層高的唐樓。今天的保德街融合了舊鋪與新店,希望它不要變得火熱,如果這裡變得太熱鬧,就不再有趣了。
看起來平平無奇,其實是別有洞天,大街內的小巷,小巷內的小店,小店內的後欄,好像Artisan Garden Cafe 內的露天座位其實是個小天井,乾淨整潔,抬頭看到高樓與大樹,香港果真是石屎森林。不過可惜的是茶。家將於月底結業,又少了一個選擇。
舊相來源: http://hkgalden.com/view/107520

Thursday, June 1, 2017
記錄日常(一) 不要亂糟糟的衣櫃
偶而看到陳曉蕾從前在專欄介紹《Daily Rituals: How Artists Work》一書,完全合我胃口。好像村上春的《身為職業小說家》,總是對書寫生活日常很有興趣,也很想知道,除了自由工作者外,甚麼人跟我一樣,喜歡看別人記錄日常工作?
很多人也會說要成為自由工作者,最重要是要有discipline。我一直也在想這個問題,正是因為我不喜歡discipline 才選擇走上這條路呢,這些年來,雖不至顛三倒四,我確實沒有過著很規律的生活,托賴還可以生存下來。直至早陣子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我第一本書,迫不得以要出動規律。然而在短短的過程中,我明白到所謂的規律,其實是要找到一種節奏,一種屬於自己的工作節奏。
自由工作者其實就是能夠掌握生活節奏,除了工作,也得安排生活瑣碎事,以今天為例,因為約了朋友中午在黃大仙午餐,於是之前先拿玻璃樽到浸會醫院,朋友的環保小隊,午飯後再到黃山仙的Green Ladies 寄賣舊衫,之後再找間Taste 入貨(因為有張Taste coupon,平日甚少幫襯) 準備之後幾天在家工作,因為長時間在家工作,儲糧是必須的。原本打算看一場電影,可是因為吃了個無味的午餐,必須以下午茶補充一下,也就坐下來吃點好東西,也看了幾頁《Daily Rituals》,的確好睇,然後也沒打算趕著看電影,趁繁忙時間前回家去了。
在忙得頭昏腦脹的日子,別說會乖乖的處理玻璃樽,執衣櫃也是奢侈的事,而換季時不執衣櫃的後果,就是搵唔到衫著!所以,我認為今天做的正是我要過的一種生活。
看完Mason Currey 這本書後再想想我的節奏。
http://masoncurre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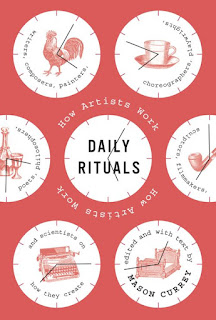
很多人也會說要成為自由工作者,最重要是要有discipline。我一直也在想這個問題,正是因為我不喜歡discipline 才選擇走上這條路呢,這些年來,雖不至顛三倒四,我確實沒有過著很規律的生活,托賴還可以生存下來。直至早陣子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我第一本書,迫不得以要出動規律。然而在短短的過程中,我明白到所謂的規律,其實是要找到一種節奏,一種屬於自己的工作節奏。
自由工作者其實就是能夠掌握生活節奏,除了工作,也得安排生活瑣碎事,以今天為例,因為約了朋友中午在黃大仙午餐,於是之前先拿玻璃樽到浸會醫院,朋友的環保小隊,午飯後再到黃山仙的Green Ladies 寄賣舊衫,之後再找間Taste 入貨(因為有張Taste coupon,平日甚少幫襯) 準備之後幾天在家工作,因為長時間在家工作,儲糧是必須的。原本打算看一場電影,可是因為吃了個無味的午餐,必須以下午茶補充一下,也就坐下來吃點好東西,也看了幾頁《Daily Rituals》,的確好睇,然後也沒打算趕著看電影,趁繁忙時間前回家去了。
在忙得頭昏腦脹的日子,別說會乖乖的處理玻璃樽,執衣櫃也是奢侈的事,而換季時不執衣櫃的後果,就是搵唔到衫著!所以,我認為今天做的正是我要過的一種生活。
看完Mason Currey 這本書後再想想我的節奏。
http://masoncurre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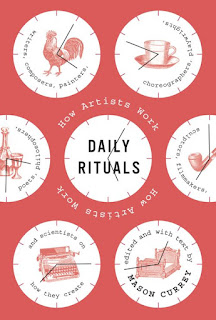
Thursday, March 9, 2017
怕老虎的楊姓朱姓馬姓牛姓街坊們
上網隨便查查,都會說因為「老虎岩」名字剎氣太大,兼且不吉利,所以改名為「樂富」。而我找到這個小故事:
話說當時住在老虎岩徙置區的居民,覺得自從搬入村後便感到諸事不順,原因是他們住在老虎的洞穴裡,特別是姓楊姓朱姓馬和姓牛的街坊們,由於姓氏諧音與相對的動物相同,而牠們都是老虎的獵物!所以非常的不吉利,於是由街坊福利會出頭,申請改名。
這是在政府檔案處無意間找到的「花絮」,因為太好笑,忍唔住要留下紀錄。 從「老虎岩」到「樂富」,一定是殖民者刻意的去歷史或現代化嗎? 我想到的卻是當年英國佬都唔明你地搞咩鬼,又幻想居民在開街坊大會時的情況。
不過,原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樂富從前叫做「老虎岩」,改名發生在1970年,四十多年,很遠嗎?是否還可以找到朱大叔楊伯馬生牛師奶問問。口述歷史真的很有趣。
話說當時住在老虎岩徙置區的居民,覺得自從搬入村後便感到諸事不順,原因是他們住在老虎的洞穴裡,特別是姓楊姓朱姓馬和姓牛的街坊們,由於姓氏諧音與相對的動物相同,而牠們都是老虎的獵物!所以非常的不吉利,於是由街坊福利會出頭,申請改名。
這是在政府檔案處無意間找到的「花絮」,因為太好笑,忍唔住要留下紀錄。 從「老虎岩」到「樂富」,一定是殖民者刻意的去歷史或現代化嗎? 我想到的卻是當年英國佬都唔明你地搞咩鬼,又幻想居民在開街坊大會時的情況。
不過,原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樂富從前叫做「老虎岩」,改名發生在1970年,四十多年,很遠嗎?是否還可以找到朱大叔楊伯馬生牛師奶問問。口述歷史真的很有趣。
Monday, March 6, 2017
古典音樂 當代創新 從《銘約》音樂會談起 (art plus March)
離開劇場那一刻,一切還在腦海中。
開始時,我們如常坐在觀眾席,面向 演奏者,第一首作品是廸恩(Brett Dean)的《卡 洛》,背 後 是 大 屏 幕,配 合影像的變化,從樂手到屏幕、從音 樂到影像,視覺、聽覺的感官逐漸被 打開。接著,觀眾離開座位,走到台 中央,隨意席地而坐,演奏的是赫斯(Georg Friedrich Haas)的《弦樂四重 奏 第 三 號 〈 暗 黑 日 夜 曲 〉》, 此 時 整 個 劇 場漆黑一片,當音樂響起,你隱約知道 樂 手 身 處 何 方,這 一 回,再 不 需 依 賴 視 覺,全然用耳朵去聆聽感受。隨後,四 位弦樂手的剪影出現在眼前,貝多芬的 F 大調弦樂四重奏響起,樂手在光影 交錯中編織弦樂聲。最後,在劇場後 方出現了12位中提琴手,他們站在觀 眾席,在指揮蔡敏德帶領下演奏廸恩的《銘約》。開首與結束,觀眾與樂手剛 好調換了位置。
古典音樂會有很多的預知,觀眾為了那 指揮那演奏家那些曲目而來,然後安 安 靜 靜 , 坐 在 觀 眾 席 上 ,上 半 場 完 結 , 休息一陣子,再繼續下半場。確實如《銘約》音樂會的設計師烏德(Folkert
Uhde)所說:「社會上沒有幾個領域會 如「古 典 音 樂 會」般,從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就沒有經驗過大轉變。」《銘約》音樂會打破了這種常規。來自 柏林的烏德是音樂會設計師,對亞洲 來說,「音樂會設計」的概念頗為陌生, 設計音樂會不只是技術上,而是整個策 展理念,關乎樂曲內容及進行步驟。在 歐洲,以嶄新形式出發的古典音樂會越 來越多,也是回應時代轉變的一個大 方向,尤其古典音樂在歐洲是歷史傳統 卻也是歷史包袱,在音樂廳出現的都 是銀髮族,樂團在社區推廣古典音樂 之餘,得更花盡心思吸引觀眾入場。除 了嘗試舉辦不同形式的音樂會,例如配 合現場管弦樂團演奏的電影放映,或 是走出音樂廳,在戶外或非正式的表 演場地舉行音樂會,近年也頗為流行。 然而,這類型的音樂會只是單從形式出 發,加一點新的內容,換個場地,始終 還是停留在「你來看看我們的音樂演 出」這個層面。音樂會設計(Concert D e s i g n)的 概 念 卻 更 為 全 面,烏 德 說:「 每 場 實 驗 的 中 心 是 觀 眾 」— — 在 「 音 樂 演 出 」 以 外 ,「 音 樂 會 體 驗 」 才 是 核 心 問題。
古典樂迷總是按圖索驥地走進音樂 廳,期待台上一場超凡技藝,扣人心弦 的演出,在此常見的音樂會形式中,獲 得的往往是一種單向的聆聽經驗。假 若 這 次《 銘 約 》如 一 般 的 音 樂 會,完 場 後,腦 內 留 下 的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畫 面,可 是從演出完至今,四首曲目的畫面仍 歷歷在目、記憶猶新。音樂固然還是 主角,但利用視覺效果和空間設計去 呈現音樂,對觀眾是新體驗,對演奏者 也 是 挑 戰 。 不 過 ,《 銘 約 》 還 是 以 作 曲 家,演奏者和指揮為主導,但今年 Art Basel 期間,Spring 工作室名為「這是 一種呈示,不是一個展覽」的實驗性活 動,便與本地多間藝術機構合作,探討 本地藝術與音樂的連結與分野1;香 港創樂團所主辦的現代學院,亦於今 年 4 月與冰島的 Cycle 音樂及藝術節 合作,讓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參與,嘗試 連 結 當 代 音 樂 、演 出 、 視 覺 藝 術 、 聲 音 藝術及建築藝術 1。從綜合的多媒體到 扣連的協作呈現,看來這個時代無論何 種領域的藝術,都再也不能孤軍作戰。


開始時,我們如常坐在觀眾席,面向 演奏者,第一首作品是廸恩(Brett Dean)的《卡 洛》,背 後 是 大 屏 幕,配 合影像的變化,從樂手到屏幕、從音 樂到影像,視覺、聽覺的感官逐漸被 打開。接著,觀眾離開座位,走到台 中央,隨意席地而坐,演奏的是赫斯(Georg Friedrich Haas)的《弦樂四重 奏 第 三 號 〈 暗 黑 日 夜 曲 〉》, 此 時 整 個 劇 場漆黑一片,當音樂響起,你隱約知道 樂 手 身 處 何 方,這 一 回,再 不 需 依 賴 視 覺,全然用耳朵去聆聽感受。隨後,四 位弦樂手的剪影出現在眼前,貝多芬的 F 大調弦樂四重奏響起,樂手在光影 交錯中編織弦樂聲。最後,在劇場後 方出現了12位中提琴手,他們站在觀 眾席,在指揮蔡敏德帶領下演奏廸恩的《銘約》。開首與結束,觀眾與樂手剛 好調換了位置。
古典音樂會有很多的預知,觀眾為了那 指揮那演奏家那些曲目而來,然後安 安 靜 靜 , 坐 在 觀 眾 席 上 ,上 半 場 完 結 , 休息一陣子,再繼續下半場。確實如《銘約》音樂會的設計師烏德(Folkert
Uhde)所說:「社會上沒有幾個領域會 如「古 典 音 樂 會」般,從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就沒有經驗過大轉變。」《銘約》音樂會打破了這種常規。來自 柏林的烏德是音樂會設計師,對亞洲 來說,「音樂會設計」的概念頗為陌生, 設計音樂會不只是技術上,而是整個策 展理念,關乎樂曲內容及進行步驟。在 歐洲,以嶄新形式出發的古典音樂會越 來越多,也是回應時代轉變的一個大 方向,尤其古典音樂在歐洲是歷史傳統 卻也是歷史包袱,在音樂廳出現的都 是銀髮族,樂團在社區推廣古典音樂 之餘,得更花盡心思吸引觀眾入場。除 了嘗試舉辦不同形式的音樂會,例如配 合現場管弦樂團演奏的電影放映,或 是走出音樂廳,在戶外或非正式的表 演場地舉行音樂會,近年也頗為流行。 然而,這類型的音樂會只是單從形式出 發,加一點新的內容,換個場地,始終 還是停留在「你來看看我們的音樂演 出」這個層面。音樂會設計(Concert D e s i g n)的 概 念 卻 更 為 全 面,烏 德 說:「 每 場 實 驗 的 中 心 是 觀 眾 」— — 在 「 音 樂 演 出 」 以 外 ,「 音 樂 會 體 驗 」 才 是 核 心 問題。
古典樂迷總是按圖索驥地走進音樂 廳,期待台上一場超凡技藝,扣人心弦 的演出,在此常見的音樂會形式中,獲 得的往往是一種單向的聆聽經驗。假 若 這 次《 銘 約 》如 一 般 的 音 樂 會,完 場 後,腦 內 留 下 的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畫 面,可 是從演出完至今,四首曲目的畫面仍 歷歷在目、記憶猶新。音樂固然還是 主角,但利用視覺效果和空間設計去 呈現音樂,對觀眾是新體驗,對演奏者 也 是 挑 戰 。 不 過 ,《 銘 約 》 還 是 以 作 曲 家,演奏者和指揮為主導,但今年 Art Basel 期間,Spring 工作室名為「這是 一種呈示,不是一個展覽」的實驗性活 動,便與本地多間藝術機構合作,探討 本地藝術與音樂的連結與分野1;香 港創樂團所主辦的現代學院,亦於今 年 4 月與冰島的 Cycle 音樂及藝術節 合作,讓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參與,嘗試 連 結 當 代 音 樂 、演 出 、 視 覺 藝 術 、 聲 音 藝術及建築藝術 1。從綜合的多媒體到 扣連的協作呈現,看來這個時代無論何 種領域的藝術,都再也不能孤軍作戰。


Monday, February 13, 2017
躍動的捷克樂章 楊納傑克 X 捷克布爾諾 (art plus Jan)
我好奇,究竟有多少人因為村上春樹而專程走到音樂廳欣賞《小交響曲》 (Sinfonietta)?
先別誤會,楊納傑克(Leos Janáček) 絕對不是村上春樹發掘出來的,一位香 港作曲家朋友這樣提醒我。不過,因為 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裡,出現了《小 交 響 曲 》( S i n f o n i e t t a ) 卻 令 楊 納 傑 克 的 名 字「 大 紅 」起 來,令 不 太 熟 悉 古 典 音樂的讀者認識這位重要的當代捷克 作 曲 家,市 場 上 也 出 現 了 不 少 收 錄 了 這 首作品的專輯。從村上春樹到楊納傑 克,如其探究這種行銷方法是否有效, 不如嘗試回到基本,想想為什麼村上春 樹要用上楊納傑克的《小交響曲》,而楊 納傑克又是怎樣的作曲家,畢竟從文學 出發推廣古典音樂也不是新鮮事吧。
孕育楊納傑克的捷克布爾諾
去年 12 月有幸走到捷克布爾諾(Brno), 捷克第二大城市,踏踏實實,用足跡去 認識楊納傑克。雖然楊納傑克不是出生 於 布 爾 諾 , 不 過 自 1 8 6 5 年 ,1 1 歲 開 始 便在布爾諾生活,不少著名的作品也都 是誕生於這個城市。楊納傑克常被形容 是「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在 70 歲前還 未完成過一首交響曲,《小交響曲》便是 在 1926 年首演,當時的楊納傑克已 72 歲,這首作品以大量的銅管樂作開端, 二十分鐘的澎湃浩瀚,這個時候,你可 以 回 到 《 1 Q 8 4 》, 思 索 村 上 春 樹 為 何 選 用這首樂曲。事實上,楊納傑克不少著 名的歌劇作品也是在晚期完成,而且也 在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首演。建於 1882 年 的 Mahen Theatre,是 歐洲 首家引用電力供應的劇院,今天劇院還保 留了當年愛廸生製造的燈泡。直至 1919 年正式成為國家歌劇院,楊納傑克的著 名歌劇,包括《Jenufa》,《The Cunning L i t t l e V i x e b 》, 還 有 《 T h e M a k r o p u l o u s Case》、《馬克普洛斯檔案》也在這裡作 首演,繼而讓他聲名大噪。
作曲家的謬思
說起這部歌劇,必然會提到作曲家的個 人 經 歷 。《 馬 克 普 洛 斯 檔 案 》 是 關 於 一個不死女伶的故事。楊納傑克晚年 愛上一名商人的妻子,年輕的 Kamila Stösslová,多年來寫了超過七百封 情 書 給 她,《Intimate Letters: Leos Janáček to Kamila Stösslová 》一 書 便是書信在 90 年代公開後結集而成。 有說正是 Kamila 激起了楊納傑克的 創作力,寫下這部出色的歌劇。回看楊 納 傑 克 的 經 歷,也 許 並 不 盡 如 人 意,特別是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上。在布爾諾 參觀他的舊居,客廳還保留了昔日的傢 具,包括一座三角琴,更找到經典樂章 的手稿。在主廳播放了關於他生平的紀 錄片,簡述了他的一生。楊納傑克晚年 才 成 名,或 許 一 直 也 有 點 不 得 志,與 太 太的關係不好,婚姻不如意,加上兒女 相繼離世,或者我們也要多謝 Kamila 的出現,所謂的繆思就是這麼一回事。
初 冬 的 布 爾 諾 ,窗 外 盡 是 白 茫 茫 ,這 一 刻,你可以到離市中心約二十分鐘車 程的中央墓園,到楊納傑克的墓前,致 謝和緬懷一番。又或者走到市中心的 Stopka Pilsner Pub,楊納傑克經常到 訪的餐廳,喝一杯最地道的捷克啤酒, 然後才走進劇院,看 100 分鐘的《馬克 普 洛 斯 檔 案 》, 欣 賞 捷 克 音 樂 , 聽 聽 楊 納傑克如何把捷克摩拉維亞獨有語言 聲調特色,編織進這齣節奏明快的現代歌劇。

先別誤會,楊納傑克(Leos Janáček) 絕對不是村上春樹發掘出來的,一位香 港作曲家朋友這樣提醒我。不過,因為 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裡,出現了《小 交 響 曲 》( S i n f o n i e t t a ) 卻 令 楊 納 傑 克 的 名 字「 大 紅 」起 來,令 不 太 熟 悉 古 典 音樂的讀者認識這位重要的當代捷克 作 曲 家,市 場 上 也 出 現 了 不 少 收 錄 了 這 首作品的專輯。從村上春樹到楊納傑 克,如其探究這種行銷方法是否有效, 不如嘗試回到基本,想想為什麼村上春 樹要用上楊納傑克的《小交響曲》,而楊 納傑克又是怎樣的作曲家,畢竟從文學 出發推廣古典音樂也不是新鮮事吧。
孕育楊納傑克的捷克布爾諾
去年 12 月有幸走到捷克布爾諾(Brno), 捷克第二大城市,踏踏實實,用足跡去 認識楊納傑克。雖然楊納傑克不是出生 於 布 爾 諾 , 不 過 自 1 8 6 5 年 ,1 1 歲 開 始 便在布爾諾生活,不少著名的作品也都 是誕生於這個城市。楊納傑克常被形容 是「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在 70 歲前還 未完成過一首交響曲,《小交響曲》便是 在 1926 年首演,當時的楊納傑克已 72 歲,這首作品以大量的銅管樂作開端, 二十分鐘的澎湃浩瀚,這個時候,你可 以 回 到 《 1 Q 8 4 》, 思 索 村 上 春 樹 為 何 選 用這首樂曲。事實上,楊納傑克不少著 名的歌劇作品也是在晚期完成,而且也 在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首演。建於 1882 年 的 Mahen Theatre,是 歐洲 首家引用電力供應的劇院,今天劇院還保 留了當年愛廸生製造的燈泡。直至 1919 年正式成為國家歌劇院,楊納傑克的著 名歌劇,包括《Jenufa》,《The Cunning L i t t l e V i x e b 》, 還 有 《 T h e M a k r o p u l o u s Case》、《馬克普洛斯檔案》也在這裡作 首演,繼而讓他聲名大噪。
作曲家的謬思
說起這部歌劇,必然會提到作曲家的個 人 經 歷 。《 馬 克 普 洛 斯 檔 案 》 是 關 於 一個不死女伶的故事。楊納傑克晚年 愛上一名商人的妻子,年輕的 Kamila Stösslová,多年來寫了超過七百封 情 書 給 她,《Intimate Letters: Leos Janáček to Kamila Stösslová 》一 書 便是書信在 90 年代公開後結集而成。 有說正是 Kamila 激起了楊納傑克的 創作力,寫下這部出色的歌劇。回看楊 納 傑 克 的 經 歷,也 許 並 不 盡 如 人 意,特別是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上。在布爾諾 參觀他的舊居,客廳還保留了昔日的傢 具,包括一座三角琴,更找到經典樂章 的手稿。在主廳播放了關於他生平的紀 錄片,簡述了他的一生。楊納傑克晚年 才 成 名,或 許 一 直 也 有 點 不 得 志,與 太 太的關係不好,婚姻不如意,加上兒女 相繼離世,或者我們也要多謝 Kamila 的出現,所謂的繆思就是這麼一回事。
初 冬 的 布 爾 諾 ,窗 外 盡 是 白 茫 茫 ,這 一 刻,你可以到離市中心約二十分鐘車 程的中央墓園,到楊納傑克的墓前,致 謝和緬懷一番。又或者走到市中心的 Stopka Pilsner Pub,楊納傑克經常到 訪的餐廳,喝一杯最地道的捷克啤酒, 然後才走進劇院,看 100 分鐘的《馬克 普 洛 斯 檔 案 》, 欣 賞 捷 克 音 樂 , 聽 聽 楊 納傑克如何把捷克摩拉維亞獨有語言 聲調特色,編織進這齣節奏明快的現代歌劇。

Friday, February 10, 2017
《The Crown》 就是愛看英國皇室故事
在回港的航班上差不多一口氣將《The Crown》 season 1 十集完成,Netflix 新增的下載功能實在是功德無量。
在小小的ipad 看《The Crown》是有點浪費,場景佈局服裝很多的細節都需要大大的屏幕,而其實《The Crown》也不是那種每集拖著尾巴要你非追看下去不可的劇集,每集也是獨立的單元。 Season 1 鎖定在1947 至 1956年,從伊利沙白二世大婚開始,到新任首相Anthony Eden 上任,引發至Suez Canal Crisis作結。 當然女皇是故事中心,每集重現不同歷史事件,從大婚,登基、Churchill 再次贏得大選,Churchill 被勸退、倫敦毒霧事件、 女皇皇夫巡迴英聯邦國家,到其妹Margaret的「不倫戀」。Peter Morgan 以Queen Elizabeth II與丈夫Philip,與Churchill,與妹妹Margaret與母親與祖母,還有捨棄皇位的叔叔Edward 之間的關係穿梭,看到女皇在沒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登基,從不懂做女皇到慢慢學習,到最後如何能為皇室而非個人下定決心,不惜與妹決裂也要否定其婚姻,由不知所措到矛盾掙扎,看著女皇十年的成長,劇集也側寫了英國社會在二戰後的發展。以真實歷史事件出發的作品總是引人入勝,因為邊看邊想,到底這些事情發生的經過是否如此,真真假假之間能引發很多的想像。
有評論說《The Crown》處理歷史不恰當,但劇集似乎是人物傳記多於歷史劇,在描繪人物方面非常立體,外型與真實人物相似自然不在話下,能把皇室的behind the scenes 展現眼前,風光背後,是女皇在君主立憲制度下不能正正常常做一個自由的人,很多的細節描寫,像登基前她戴著那個重重的后冠在練習、馬不停蹄的外訪笑到面部抽筋,有一集還說到她要請私人補習,因為她發覺自己根本從來沒受過正常教育,甚麼常識也沒有。現代社會裡的君王,註定是怪胎,甚麼私人問題都變成公眾,皇妹結婚如是,皇夫揸飛機亦是。女皇的職責是「do nothing , keep silent」,她是The Majesty,而不是wife, mother 與daughter,即使她如何支持妹妹的婚事,卻也沒辦法成全,被誤解也不能自辯,那種身不由己其實怪可憐。吸引我的劇集往往是寫人寫得有血有肉,《The Crown》讓我看到這個只能do nothing 的女皇如何從一個人慢慢變成”half people”, 如那個放棄皇位的Edward 說:
“half –people….. the two sides within us, human and crown engaged in a fearfull civil war, which never ends”
那些反對皇室制度的人大概對這些作品嗤之以鼻,但不能否認英女皇的確是20世紀最傳奇人物之一,加上我等殖民地長大之人,對英女皇以至皇室有著莫明的親切,這一點是沒法否定的真實情感,以至她的故事總是吸引我的注視,也不諱言是帶點偷窺感覺。是以看過Peter Morgan 的電影《The Queen》,電視《The Crown》後,也非常期待到戲院看NT Live, 2013年的劇場作品《The Audience》。
在小小的ipad 看《The Crown》是有點浪費,場景佈局服裝很多的細節都需要大大的屏幕,而其實《The Crown》也不是那種每集拖著尾巴要你非追看下去不可的劇集,每集也是獨立的單元。 Season 1 鎖定在1947 至 1956年,從伊利沙白二世大婚開始,到新任首相Anthony Eden 上任,引發至Suez Canal Crisis作結。 當然女皇是故事中心,每集重現不同歷史事件,從大婚,登基、Churchill 再次贏得大選,Churchill 被勸退、倫敦毒霧事件、 女皇皇夫巡迴英聯邦國家,到其妹Margaret的「不倫戀」。Peter Morgan 以Queen Elizabeth II與丈夫Philip,與Churchill,與妹妹Margaret與母親與祖母,還有捨棄皇位的叔叔Edward 之間的關係穿梭,看到女皇在沒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登基,從不懂做女皇到慢慢學習,到最後如何能為皇室而非個人下定決心,不惜與妹決裂也要否定其婚姻,由不知所措到矛盾掙扎,看著女皇十年的成長,劇集也側寫了英國社會在二戰後的發展。以真實歷史事件出發的作品總是引人入勝,因為邊看邊想,到底這些事情發生的經過是否如此,真真假假之間能引發很多的想像。
有評論說《The Crown》處理歷史不恰當,但劇集似乎是人物傳記多於歷史劇,在描繪人物方面非常立體,外型與真實人物相似自然不在話下,能把皇室的behind the scenes 展現眼前,風光背後,是女皇在君主立憲制度下不能正正常常做一個自由的人,很多的細節描寫,像登基前她戴著那個重重的后冠在練習、馬不停蹄的外訪笑到面部抽筋,有一集還說到她要請私人補習,因為她發覺自己根本從來沒受過正常教育,甚麼常識也沒有。現代社會裡的君王,註定是怪胎,甚麼私人問題都變成公眾,皇妹結婚如是,皇夫揸飛機亦是。女皇的職責是「do nothing , keep silent」,她是The Majesty,而不是wife, mother 與daughter,即使她如何支持妹妹的婚事,卻也沒辦法成全,被誤解也不能自辯,那種身不由己其實怪可憐。吸引我的劇集往往是寫人寫得有血有肉,《The Crown》讓我看到這個只能do nothing 的女皇如何從一個人慢慢變成”half people”, 如那個放棄皇位的Edward 說:
“half –people….. the two sides within us, human and crown engaged in a fearfull civil war, which never ends”
那些反對皇室制度的人大概對這些作品嗤之以鼻,但不能否認英女皇的確是20世紀最傳奇人物之一,加上我等殖民地長大之人,對英女皇以至皇室有著莫明的親切,這一點是沒法否定的真實情感,以至她的故事總是吸引我的注視,也不諱言是帶點偷窺感覺。是以看過Peter Morgan 的電影《The Queen》,電視《The Crown》後,也非常期待到戲院看NT Live, 2013年的劇場作品《The Audience》。
重新愛上歐洲的冬天-聖誕限定
總是避開歐洲的冬天,四點天黑未免讓人太沮喪了。這次公幹卻讓我重回歐洲的冬,可能是有備而戰,身心都有準備,日照短沒問題,天黑便天黑吧,預計不到的是遇上了初雪,白茫茫的雪地與光禿禿的枯樹,是蕭瑟卻讓我感到寧靜平和,晚上聖誕市集亮起的燈飾卻又添上美好與歡樂。
作為非教徒兼帶點cyncial的人,聖誕與我又何干?在香港從來只是空洞的假期與假期,依然是吃喝玩樂,而且好像要必須這樣過。這幾天逛聖誕市集,雖是大同小異,但這樣的聖誕才讓我有感覺,這裡的聖誕不是空洞的節日,是宗教習俗歷史的傳承,聖誕是屬於歐洲的,Christmas is something。到了24, 25,全世界回家,很好。
再過一個月,又冷一點,雪又多一點,這樣的冬天便不可親。能夠在旅途上遇上初雪與濃烈的節日氣氛已很滿足,做旅客,又不用剷雪。
作為非教徒兼帶點cyncial的人,聖誕與我又何干?在香港從來只是空洞的假期與假期,依然是吃喝玩樂,而且好像要必須這樣過。這幾天逛聖誕市集,雖是大同小異,但這樣的聖誕才讓我有感覺,這裡的聖誕不是空洞的節日,是宗教習俗歷史的傳承,聖誕是屬於歐洲的,Christmas is something。到了24, 25,全世界回家,很好。
再過一個月,又冷一點,雪又多一點,這樣的冬天便不可親。能夠在旅途上遇上初雪與濃烈的節日氣氛已很滿足,做旅客,又不用剷雪。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